洛克王国凡雀,李清云真的活了256岁吗?
不请自来客。
笔者不想与人争论。只是主观阐述自身观点。希望有识之士不要喷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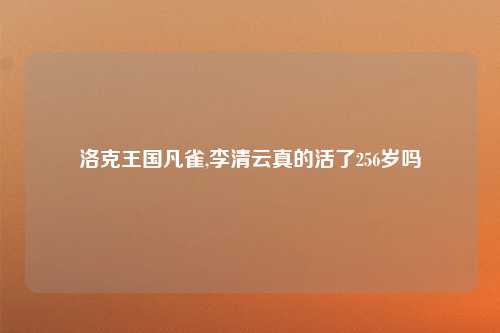
其实这位老人也挺可怜……被人借以高寿报道利用。(真要是养命到了这种程度的高真。没有几个会抛头露面。早就找个福地养着了。)
这个就和珍奇动物似的。人们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稀罕舞,就会动了心思,借着这个事情开始到处宣扬展示,追逐利益……这种情况不少啊。
在那个没有明确记录人们出生年月日的时代。其实是说啥是啥。打个比方:笔者要是生活在那个时代,背井离乡,生的仪表堂堂,懂点养命功夫、幻术技巧和拳脚功夫,说话高深莫测,再有点心理和社会学知识,口才好。笔者说自己是得道仙人都可以。
不要说当时了,就是现代也会有一帮子徒子徒孙……
至于年龄三百四百的随我说了。要证据好啊。给他们搞篇县志记载,找来几个人作证。信的人多了也就成真了……
现在信佛的有多少见过佛陀真容?(看过塑像自己幻想的不算)。而且就认为那些泥塑贴金的塑像就一定是佛陀模样?但是很多人都这样说,信了也就真了。不信也就是假的。
这位李清云老人。到底生理年龄活了多少……是个尘封在时间里的秘密了。但是想要让他变成板上钉钉的事实。只要国家承认,大肆宣扬一下,过上几年也就真了。
至于老人为何这么说,可能是信命。为了躲灾直接加了寿数……
就这样……
一家之言。一笑了之。
祝身安体泰福寿安康。
宋词第一人?
个人认为周邦彦当为两宋词人第一。下面这篇文章是我高中时遍览两宋词人词集,对比之后,在周邦彦《清真集》后写下的读书感想。尽管现在看来,高中时的文笔议论尚多有不足,但在我心目中,周邦彦是两宋词人第一的看法,却没有改变,词学正宗,当属清真!今仅附录当年的读书笔记,一二感想,聊供读者参考。
历来谈词,必推两宋;两宋之间,必推清真。大晟乐府,独步天下;顾曲名堂,风流自命;词人甲乙,早有定论。
强焕《毛刻片玉词序》云:“公之词,其模写物态,曲尽其妙。”刘肃《朱刻片玉集序》谓:“言言皆有来历,真足冠冕词林。”周济《介存斋论词雑着》则称:“后有作者,莫能出其范围。”《白雨斋词话》谓:“顿挫之妙,理法之精,千古词宗,自属美成。”亦峰《词坛丛话》亦云:“美成乐府开合动荡,独绝千古。”蒋兆兰《词说》更推之曰:“浑厚和雅,冠绝古今,可谓极词中之圣。”近人王静安《人间词话》于清真尚有微词,而后来之《清真先生遗事》则极称:词中老杜,则非先生不可;两宋之间,一人而已!
噫,古往今来,片玉一集,群推作手,公认大家,一代词宗,不容诬也!今观其流传之作,小令长调,无一不佳。布局精工,造句炼字,可称神来之笔;音韵和谐,精壮顿挫,已成广陵绝调。
集中常有艳情人语,妙不可言,缠绵婉转,动人心神,漾人情魄,真是“别有一种姿态,句句洒脱,香奁泛语,吐弃殆尽”(《白雨斋词话》)。诸如《少年游》(并刀如水)结句:“马滑霜浓,不如休去,直是少人行”,缠绵悱恻,难分难舍之情真令人“魂摇目荡矣”(《皱水轩词筌》);《望江南》(歌席上)“浅淡梳妆疑见画,惺忪言语胜闻歌”一联,似朴实艳,不用一华丽修饰之字,而自风华艳极,刻画入微,更足动人;《满路花》(金花落烬灯)“愁如春后絮,来相接。知他那里,争知人心切,除非共伊说。不成也还,似伊无个分别”几句,似百无聊赖之句而实情深意极之语,远胜耆卿《昼夜乐》(洞房记得初相遇)中“对满目,乱花狂絮。直恐风光好,尽随伊归去”之句;《意难忘》(衣染莺黄)“些个事,恼人肠,试说与何妨。又恐伊、寻消问息,瘦减容光”之句言情细腻,体贴入微,至于张玉田《词源》批美成此等词“所谓淳厚风日变成浇风也”,则甚为荒谬,此等词岂不温厚耶,此等词岂不朴质耶;《风流子》(新绿小池塘)结句:“天便教人,霎时厮见何妨”,则可谓一往情深矣,按沈义父《乐府指迷》竟谓此等句“轻而露”、“亦是词家病,却不可学也”,此说甚误,况夔笙《蕙风词话》卷二【壹柒】则已批其“非真能知词者”,不须我辈多言;《蝶恋花》(月皎惊乌栖不定)“唤起两眸清炯炯,泪花落枕红棉冷”之句情景交融,情真景美,使人为之黯然销魂矣;《解连环》(怨怀无托)“拚今生,对花对酒,为伊泪落”,非深情至性者不能道也,按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谓:“美成能作景语,不能作情语;能入丽字,不能入雅字”,则又属皮相之见,实无足置辩;《尉迟杯》(随堤路)结句云:“有何人,念我无憀,梦魂凝想鸳侣”似拙实厚,意切情真,尤耐人寻味;《庆春宫》(云接平岗)结句云:“许多烦恼,只为当时,一饷留情”,真可谓“专作情语而绝妙者”(《人间词话》),不见多也。陈郁《藏一话腴》 谓:“清真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,贵人学士,市嬛妓女,知美成词可爱”,大抵指此类意切情真之作也。清真造词炼字亦精妙无比,锤炼之处尤以对偶最为明显,如“梅风地溽,虹雨苔滋”、“渭水西风,长安乱叶”、“风灯零乱,少年羁旅”、“一箭风快、半蒿波暖”、“异乡淹岁月,醉眼迷登眺”、“事逐孤鸿尽去,身与塘蒲共晚”之类是也。近人龙沐勋《词学十讲》第六讲《论对偶》即称:“兼用领字格并取得‘奇偶相生’妙用的,要以《清真集》的变化为最多。”
然先生流传之作,备受推崇,让后人望尘莫及者,又当推其长调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即云:“(清真词)长调尤善铺叙,富艳精工”,陈亦峰《云韶集》亦谓:“美成长调,高据峰巅,下视群山,尽属附庸”,近人王静安于早作《人间词话》不甚许清真,然亦云:“长调自以周、柳、苏、辛为最工。”细玩《请真集》,长调之作伙矣,精矣,铺陈排比,严于守律,错落有致,跌宕起伏,情景交融,大气磅礴,富艳精工,允为词宗。《西河·金陵怀古》(佳丽地)一章,沉郁顿挫,满纸苍苍,前人佳句,点化如神,女墙淮水,兴亡斜阳,金陵怀古,此为绝唱!《草堂诗余正集》所谓“介甫《桂枝香》独步不得”,信哉!《花犯》(粉墙低)一章,抚今追昔,迂回反复,精致细密,斧凿无痕,谭复堂《谭评词辩》谓:“‘相将去’二句,如颜鲁公书,力透纸背”,正缘此二句收笔逆转,老健有力耳。全词由花及人,寄身世沉浮,仕宦飘零之感于咏梅之中,有情有景,能入能出,尤为高绝,昔人以此为“梅词第一”(黄苏《蓼园词选)》,“古今绝唱,读之可悟词境”(《乔大壮手批<片玉集>》,誉虽高而实所归也。《瑞龙吟》(章台路)一章章法错落反复而不嫌板滞,首尾兼顾而沉郁有力,真可谓“词境浑融,大而化矣”(陈洵《海绡说词》)。《解语花·元宵》(风消焰蜡)一章行云流水,潇洒自如,足可见当日京师之繁盛,允为咏节序词之佳构,“桂华流瓦”四字风华有致,王静安《人间词话》惜其以“桂华”二字代月,其旨宝源钟嵘《诗品·序》中“观古今胜语,多非补假,皆有直寻”一句,然非为的解。今人吴小如《莎斋笔记》之《诗词札丛》中论“桂华”一语之妙尤详,可供参观。《兰陵王》(柳阴直)一章感慨悲凉,极尽沉郁顿挫之旨,离情别意,黯然凄恻,融情于景,绮丽奇崛,笔力之高,已臻绝境,片玉一集,以此压卷!王灼《碧鸡漫志》谓其能得《离骚》之旨,信哉。《大酺》(对宿烟收)一章亦向称名篇佳构,章法奇崛,陈洵《海绡说词》析之甚祥,并叹“美成信天人也”,可资参观,“流潦妨车毂”五字向称奇构,不需我辈多言。《六丑·蔷薇谢后作》(正单衣试酒)一章诚如夏敬观所云“一气贯注,转折处如天马行空”(龙沐勋《唐宋名家词选》引),羁旅漂泊,情肠愁思,缠缠绵绵,吐露不尽,“怒春”十三字百转千回,笔力老辣,古今共赏。全词“笔态飞舞,反复低徊”(《云韶集》),“后来作者,罕能继踪”(《芬陀利室词话》),洵非溢美之词。《浪淘沙》(画阴重)一章“精壮顿挫,已开北曲先声”(《人间词话》),纵观全词上下相融无痕,笔力之大难以想象,笔迹之绝无从琢磨,可谓神品矣!昔人尝以耆卿、清真并称,然窃以为耆卿固为作手,慢词长调佳构亦伙,《曲玉管》(陇首云飞)、《雨霖铃》(寒蝉凄切)、《采莲令》(月华收)、《卜算子》(江风渐老)、《浪淘沙》(梦觉,透窗风一线)、《双声子》(晚天萧索)、《二郎神》(炎光谢)、《醉蓬莱》(渐亭皋叶下)、《抛球乐》(晓来天气淡淡)、《戚氏》(晚秋天)、《夜半乐》(冻云黯淡天气)、《望海潮》(东南形胜)、《玉蝴蝶》(望处雨收云断)、《八声甘州》(对潇潇暮雨洒江天)、《透碧霄》(拆桐花烂漫)、《倾杯》(鹜落霜洲)诸作固为大手笔,时或笔力健拔、情景相融,羁旅漂泊、登高望远,离情别绪亦时时动人。然至于沉郁顿挫、苍凉悲壮、音声相和、词律谨严,则于清真先生尚隔一层矣!即以体物言情之作而言,虽皆能情真意切,然耆卿于遣词造句,忠厚缠绵,坚贞深情之处亦未及清真,刘熙载《艺概·词概》谓美成词“只是当不得一个贞字”,实是瞽言刍议,无足置辩。陈锐《袌碧斋词话》谓:“屯田词在院本中如《琵琶记》、清真词如《会真记》;屯田词在小说中如《金瓶梅》,清真词如《红楼梦》。”譬喻颇新,殊耐玩味,二家一贵雅一粗俚之风格亦明矣。大抵南北两宋,词家林立,真堪与清真对峙颉颃者,唯一稼轩而已。此二子一为婉约之组,一为豪放之宗,历来早有公论。“辛稼轩,词中之龙也”(《白雨斋词话》卷一【陆叁】)!稼轩词满纸龙虎风云之气,魄力之大、笔力之健、词章之富、冠冕两宋,后世之俗子胸襟难以窥其堂奥。陈匪石《宋词举》谓清真先生“集词学之大成,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,凡两宋之千门万户,《清真》一集,几擅其全。”窃以为若能合《清真集》与《稼轩长短句》,则可以全两宋之千门万户矣!至于晏氏父子、秦淮海、李易安、姜白石诸子未及清真处以及苏东坡、黄山谷、张芦川、陆放翁、张于湖未及稼轩之缘由,限于篇幅,不多论矣。
又有一事或可略论及之,即自古笺注诗者伙矣,诸如王琦笺注《李太白集》、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、三家评注《昌谷集》、冯应榴《苏文忠公诗集合注》等是也,而笺注词者则鲜矣。然近世以还,笺注词者亦渐伙矣,名家善本层出不绝。诸如邓广铭《稼轩词编年笺注》、夏承焘、吴熊和《放翁词编年笺注》、夏承焘《姜白石词编年笺注》及徐培均之《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》、《李清照集笺注》等是也。更有青出于蓝者,如陈书良之《姜白石词笺注》是也。至于笺注《清真集》之善本,则应推今人罗忼烈之《清真集笺注》一书。今人笺注词者多足以补前修所未逮,偶有不足之处,限于篇幅,亦不多论矣!
不孝的儿郎是什么意思?
现在大多数的人都居住商品房,对于什么东厢房西厢房还有什么房屋方位,都没有太多的讲究与注意了,最多就是看通风与采光而已,首选就是坐北朝南的方向。
以前的老房子,尤其是北方的房子格外注重坐北朝南,而通常来说,这个方位的房屋都尽可能留给自己的父母老人,因为这样的房子采光与通风条件是最好的。
北方大多数的住房,就是那种传统的四合院,因此也被分成了东屋、西屋、南房与北房,不过因为地势条件等原因,并不是所有的房子都能够坐北朝南这样布局。
如果是条件有限,一般一片院落住宅当中,只有几个房间是坐北朝南的,即便是皇宫里也有阴暗潮湿,通风采光条件都不怎么样的地方,这也是实在没办的事情。
人都愿意住在通风条件跟采光好的房间里,因为住着舒服也不容易生病,而那些条件不太好的房间,如果家里人口少,就用来做杂物间什么的,很少用来当做是主屋。
家里的东屋与南房,通常都条件不太好,尤其是南房,采光很差也不通透,而东屋与西屋往往是用作厢房,这些屋子平常尽可能不住,要么都是让晚辈居住,不太让长辈居住。
不仅如此,因为传统的建筑都讲究次序,一个四合院当中的正屋是主,之后是西屋,也就是西厢房,再来是东屋,也就是东厢房,最后才是前方的南房。
大家族当中,首先居住在正房西边的房间,其次是正房东边,以长幼次序来安排,最末的才是南房,如果家里安排老人长辈住在东屋或者南房,那完全就是颠倒长幼实属不孝。
现在家里安排老人房的时候,通常也都是将采光比较好的房间留给老人,一般主卧仍旧还是条件最好的,而像是朝北的房间,往往用作杂物间或者是书房、客房之类。
从古至今,各种对于老人对于长幼次序之类的细节讲究无处不在,要是家里随便安排老人的住处的话,很可能被视作对长辈老人的不敬,那就是不孝,所以才说东屋南房不孝儿郎。
鸟偏旁在古代指什么?
鸟偏旁是长尾巴的鸟
鸟,长尾禽总名也。象形。凡鸟之属皆从鸟。
隹,鸟之短尾总名也。象形。凡隹之属皆从隹。
古文中长尾的飞禽叫“鸟”,短尾的叫“隹”。
凡是鸟属的字为鸟部,如:鸦、鹬、鹜、鹭;
凡是隹属的字为隹部,如:雀、隼、鸡(鸡繁体)、雉(野鸡)。
鸟,又称作鸟儿。定义:有羽毛几乎覆盖全身的卵生脊椎动物。
字典解释:脊椎动物的一类,温血卵生,用肺呼吸,几乎全身有羽毛,后肢能行走,前肢变为翅,大多数能飞。
在动物学中,鸟的主要特征是:身体呈流线型,大多数飞翔生活。体表被覆羽毛,一般前肢变成翼(有的种类翼退化);胸肌发达;直肠短,食量大消化快,即消化系统发达,有助于减轻体重,利于飞行;心脏有两心房和两心室,心搏次数快。
体温恒定。呼吸器官除具肺外,还有由肺壁凸出而形成的气囊,用来帮助肺进行双重呼吸。
后周开国皇帝郭威为何将天下交给养子柴荣?
柴荣虽是郭威养子,但与他也有亲戚关系,并共同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,两个人情同父子,而且郭威亲儿子在反汉的时候在开封被杀,柴荣是唯一的,也是最合适的继承者。
甚至,即使郭威亲儿子在,郭威也很有可能传位给柴荣。因为按照五代十国混乱的继承情况,不认宗法秩序,只认拳头大有理(甚至到了北宋初年,赵匡胤传位给赵光义也有这样的考量),而柴荣无异是那个拳头最大的人。
柴荣,是整个五代十国独一档的存在,是唯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皇帝。所以郭威选择柴荣作为继承人,是做合适的选择。
01完美继承者周世宗柴荣,生于公元921年10月27日,邢州尧山县(今河北隆尧)人,后周太祖郭威外甥、养子,后周第二位皇帝,也是五代十国唯一一位具有建立大一统王朝潜力的皇帝。
柴荣出生的时候,后梁和后唐早已经化作了历史尘埃,后续建立的后汉和后晋两个朝代不仅国祚急促,而且国力孱弱,越发无法应对来自北方契丹人的威胁。后晋建立者石敬瑭更是对契丹称臣,认其为父,割让了幽云十六州,让中原王朝失去了对抗关外势力最大的凭借。
直到后周建立之后,中原王朝才开始逐渐凝聚起力量,反击北部契丹人的威胁。到了世宗柴荣继位之后,外平诸敌,隐然有大唐之风;内修文法,重建制度和文化,可以说是五代十国独一档的存在。
五代其他枭雄人物,朱温、李存勖、李嗣源等人,全都是武德充沛之人,但对文治并无特别大的建树。如果生在盛世,这些人也许会是极好的大将。
但是,唯有世宗柴荣,明白文治的重要性,也懂得如何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帝国,这就是世宗柴荣和其他所有五代十国枭雄的最大区别。
代十国礼乐崩坏,在太平盛世也刀光剑影的皇位继承更是危险非常。从后梁建立开始,李存勖是唯一一个以亲儿子的身份顺利继位,而且有所作为的。但如果把范围稍微扩大,从下一代继承者角度来看,柴荣无疑是五代时期最完美的继承者。
首先就是柴荣与后周太祖郭威的关系亲密。柴荣是郭威的养子,但也是郭威的外甥,年幼的时候,柴荣跟着自己的姑姑到了姑父郭威身边。《旧五代史》记载:
(柴荣)年未童冠,因侍圣穆皇后,在太祖(郭威)左右……(柴荣)悉心经度,财用获济,太祖甚怜之,乃养为己子。
威身为柴荣的姑父,本身就与柴荣有亲戚关系。当柴荣来投靠他的姑姑的时候,郭威看他机灵谨慎,很怜爱他,加上当时没孩子,就把柴荣当做了自己的养子。所以郭威与柴荣虽不是父子关系,却和父子关系相当。
其次就是柴荣自身天赋满满,给了郭威很大的支持,资历威望十足。郭威出身低微,柴荣到他身边的时候,他还远没有后来的显贵。
但也因为如此,柴荣经历了郭威一步步崛起的过程,并很早就开始替郭威处理事情,这份资历,在后来郭威手下诸将中也是独一档的。
天福十二年(947年),刘知远刚建立后汉政权,郭威被任命为枢密副使,柴荣此时已经27岁,也被任命为左监门卫大将军。
等刘知远去世,郭威成为了顾命大臣,任邺都留守、天雄军节度使,柴荣则升任了天雄军牙内指挥使,掌管郭威的亲军。在郭威以清君侧名义杀向开封的时候,留守大本营邺都的正是柴荣。
等后周建立,柴荣更是委以重任。这里还有一个意外,就是在郭威起兵反后汉的时候,他的大部分家人都在开封,并被杀死,其中也包括郭威的几个亲儿子。
正因如此,等后周一建立,柴荣就得以以皇子的身份拜镇宁军节度使、澶州刺史,等到了广顺三年(953年)三月,柴荣被加封为晋王,正式从地方调入中央,担任了京城开封府府尹。
所以,在柴荣接任后周皇位之前,他已经跟随郭威十余年。在十余年中,他与郭威一起经历过低微时候的艰难,也一起经历过起兵反汉时候的危险。
后周建立之后,又直接以皇子身份历任地方大员、军镇节度使、京城开封府一把手、判内外兵马事等要职,经历丰富,名望深重。
与郭威关系亲密,情同父子,资历威望十足,又正值壮年,和后梁、后晋、后汉等朝的继承人相比,柴荣可谓是成色十足。
即使和李存勖相比,他也多了一份治理地方的经验,而不单纯是征战四方的武将,可谓是最完美的接班人。
所以,当显德元年(954年)正月,郭威病重之后,后周内部并没有多少王位交替之时的刀光剑影。正月17日,郭威驾崩,正月21日,柴荣按照遗诏,在郭威灵前继位,是为周世宗。
02“十年”拓天下后周以击败后汉立国,但后周建立之后,四周还有不少强敌,其中,占据河东一带的刘崇是最为危险的一个。刘崇是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的弟弟,刘知远建国之后,把刘崇任命为河东节度使。
读过前面下路符的《五代十国群英传》的读者应该知道,河东一带是一处战略要地,本身有黄河、太行山等险要,易守难攻。同时又俯瞰中原、河北,面对北方关外的辽国也能够自持。刘知远把刘崇任命为河东节度使,就是要为后汉提供一个有力支持。
一定程度上,这个目标实现了,后汉灭亡之后,刘崇在太原称帝,史称北汉,并不断与后周交战,复制了几十年前梁晋争霸的故事。
但刘崇远没有李克用、李存勖父子治下的河东来的兵多将广,郭威和柴荣建立的后周也比后梁强大的多。刘崇为了复兴后汉的基业,竟然向辽国乞援,并约为父子之国,称辽朝皇帝为叔叔。
在辽朝的援助之下,刘崇发动了数次与后周的大战,但依然是胜少负多,终于,郭威的去世给了刘崇一个绝好的机会,他再一次发动大军南下,妄图把握机会重创后周,周汉高平之战爆发。
显德元年(954年)2月,柴荣刚刚继位,刘崇亲自率兵三万,加上辽国支援的万余骑兵,一起南下进攻后周重镇潞州。潞州也是我们熟悉的地方了,从梁晋争霸开始,潞州、泽州就是双方必争之地,这次也是如此。
听到后汉、辽国大军压境的消息后,后周群臣认为柴荣刚继位,最好能在京城留守,稳定大局。这其实是一个很中肯的建议,但柴荣不是常人,他说:“这次刘崇趁我年少新立,有一举击败我朝的意图,所以他一定亲自来战,我也必须亲自会会他!”
随后,柴荣不顾大臣反对,决定御驾亲征,而这个决定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高平之战的结局。2月,契丹人也到了太原,和刘崇的北汉军合为一处,挥师南下,并在太平驿击败后周泽潞节度使的军队,包围了后周重镇泽州(今山西晋城)。
3月10日,周军在柴荣的率领下开始北上,并在泽州高平附近与后汉军相遇,双方展开了一场残酷的大战。在双方对决开始之后,周军的右翼竟然不战而退,后周面临溃败的危险,这个时候,柴荣不顾危险亲自督战,后周军队终于止住颓势开始反击。
这一战也是张永德、赵匡胤等后周军中实力派的成名之战,在柴荣冒死督战之下,张永德、赵匡胤等率领禁军迅速跟上,辽军与后汉貌合神离,看后周军队拼死进攻,自动退却了。
这个时候,周军殿后的军队终于赶上,和柴荣兵合一处,再破北汉,追击到高平附近,北汉军队大败而归,辎重和尸体布满山野,后周军队取得了一场大胜。
此战之后,柴荣地位得到彻底的巩固,他为了整肃军纪,斩杀了负责右翼的将领等七十余人,同时重赏了李重进、张永德、赵匡胤等人,后来这些人都成为了后周大将。
高平之战的胜利,宣告了后周的强势崛起,也宣告了在后梁和后唐之后,另一个足以和辽国掰手腕的中原王朝的崛起。高平之战虽然后周大胜,但柴荣也认识到了周军的缺点,命令赵匡胤招募天下壮士,经过严格筛选之后,组建了虎狼之师-后周殿前禁军。
击败后汉之后,柴荣开始着手剿灭其他势力。显德二年(955年)7月,柴荣安排后周大将向训、王景等人率军西征后蜀,虽然前期作战吃力,但后周实力远在后蜀之上,到了十一月,后周攻克了秦、成、阶、凤四州,后蜀国势大衰。
在征讨后蜀取得战果的同时,柴荣又把目光对准了南边,准备亲征南唐。南唐是十国中面积最大、经济最发达的割据势力,版图一度囊括了今天江西、安徽、江苏、福建、湖北和湖南等省,全部是膏腴之地,人口近500万。
柴荣在位期间一共发起了3次攻唐之战。显德二年(955年)11月,攻取南唐滁州、扬州等地,显德四年(957年)2月,再度南征,攻取寿州,显德五年(958年)正月,再次大败唐军。
在后周的不断进攻下,南唐节节败退,南唐不得不尽献江北之地,而且自去国号,改以后周为正朔,用后周纪年,并迁都洪州。经过三次打击,南唐也一蹶不振,对后周再也没有了威胁。
而柴荣在位期间最重要的战争,就是北上与辽国在河北的大战。显德六年(959年)经过5年的准备,柴荣终于对最强大的敌人,已经建立辽国的契丹人发起了进攻,目标是已经被割让24年,严重威胁中原王朝的燕云十六州。
显德六年4月,柴荣亲自率领大军北伐辽国,经过一系列的军队建设和国力建设,此时的后周国力强盛,军容壮阔。与之相反,此时辽国正是辽穆宗统治时期,政局动荡,士民离心。
辽国甚至不得不放弃了从耶律阿保机开始的南下政策,采取防守姿态,联合北汉等政权对抗后周。
所以当柴荣率军北伐的时候,后周大军直入辽境,可谓是势如破竹,所击者服、所攻者破,甚至不少城池守将直接就出城投降:
至宁州,辽宁州刺史王洪以城降;至益津关,守将终廷晖举城投降;至瓦桥关,守将姚内斌以城降;至莫州,刺史刘楚信举州投降。
到了五月,瀛州刺史高彦晖以本城归顺。同时,后周义武节度使孙行友攻克易州(今河北易县),擒获辽易州刺史李在钦。先锋都指挥使张藏英破在瓦桥关北破辽骑兵数百人,攻下固安县……
不到五十天,后周大军连收三关三州,到了五月丙午日,柴荣大会诸将,准备乘胜夺取幽州(今北京市),这个燕云十六州的核心城池!
也许很快,后周就能收复燕云十六州、重建中原王朝北部最重要的防线,甚至出关进攻辽国也并非不可能!
但就在此时,柴荣病倒了。
显德六年(959年)6月,柴荣因病回到了开封,同月,后周军队甚至已经攻克了北汉的辽州,但柴荣再也等不到收复燕云十六州的那个时候了,同年7月27日,后周世宗柴荣继位仅6年后,于开封万岁殿驾崩,终年39岁。
03“十年”养百姓柴荣在南北征伐的同时,还注意对内的经济建设,而这也是他“十年养百姓”目标的具体体现。
在柴荣继位之后,他很快着手澄清吏治,整顿禁军,组建了一只能征善战的虎狼之师。同时,在兴修水利、均定田赋、发展经济、人才选拔、重建制度和礼教等方面,都有非常大的建树:
显德元年(954年)11月,柴荣命宰相监筑河堤,兴修水利;
显德二年(955年)2月,下诏限制寺院发展,强制僧尼还俗;
显德三年(956年)10月,下诏允许盐铁通商,兴建盐场,促进经济发展;
显德四年(957年)10月,正式规定后周的科举制科为三种科目,理清人才选拔制度,为后周源源不断供给人才;
显德五年(958年)5月,命人制定《均田图》,核准田赋,重建帝国的赋税征收;
显德六年(959年)1月,命王朴校订律准,重建礼乐秩序,又搜求佚书,雕刻古籍,大兴文教……
正如欧阳修所说:
世宗区区五六年间,取秦陇,平淮右,复三关,威武之声震慑夷夏,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之士,考制度、修《通礼》、定《正乐》、议《刑统》,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。
柴荣还非常注意对人才的选拔,五代十国并非没有人才,只不过是缺少伯乐。他选拔范质、李谷、王溥等人为相,即使到了宋太祖时期也获得了重用,是能臣干吏;他任用的王朴,撰写《平边策》一文,成为后周,乃至北宋平定乱世的指导方针。
更不用说张永德、赵匡胤等禁军将领,也是能征善战之人,赵匡胤后来更是成为了北宋的开国君主。
这一切,都是柴荣远超其他五代十国皇帝,甚至远超其他大一统王朝皇帝的地方。
04再有十年,可致太平柴荣病逝于公元959年7月27日,后周显德六年,此时距离他立下“十年拓天下,十年养百姓,十年致太平”的宏伟目标,不过走了五分之一不到。
在短短6年的时间中,他北阻辽国、压制北汉,南击后蜀、削弱南唐,为后周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发展基础,使后周“威武之声震慑夷夏”。
更重要的是,他在位期间还注意从制度上进行突破,发展农业、兴修水利,注意对人才的挖掘和人才选拔制度的建设。
这些事情,远远超过一个只是统一北方的帝国需求,这是一个足以重建汉唐的帝国的基础,是一个正在冉冉升起的大一统帝国的雏形!
而这,正是柴荣超越五代十国是他枭雄最重要的地方,他眼中看到的,不仅仅是刀兵狼烟,更是一个宏伟的崭新帝国蓝图。如果果真柴荣真的能有三十年的时间,一个统一的大帝国是很有可能出现在神州大地之上的。
可惜的是,这一切,都化作了“病龙台”上的不甘与遗憾,和我们后人无尽的遐想。
